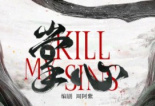台劇《非殺人小說》原著小說目前沒有電紙版,想要閱讀紙本版的可以在部落格來購買。

作家兼記者李桐豪的短篇作品《非殺人小說》曾榮獲林榮三文學獎,故事以一宗公寓離奇的空姐命案為開端,在一對伴侶看似平靜如水的生活中掀起洶湧暗潮。從解謎到真相大白的過程中,這對伴侶之間過往的矛盾、當下的猜忌逐漸浮上舞台,表面寫的是殺人與案件推理,內核卻是探尋一段愛情關係裡彼此、自我與人生種種方面的拉扯。全篇僅有一萬字,但精巧混合懸疑、推理、愛情多種類型元素,李桐豪一貫的犀利筆鋒,加上精準而明快的推進節奏,寫出了深度與娛樂性兼具的故事。
台劇《非殺人小說》原著小說節選
星期四,猴子去考試
張先生向來循規蹈矩,人生中最大的罪過不過是在圖書館借來的書畫線寫字,然而下班在自家公寓大樓門口看見警車,心臟還是猛烈地跳動起來。
警車車頂警燈閃爍,左紅右藍。在出版社當編輯的張先生想起以前編過一本科普書,知道藍紅雙色是冷暖兩色系的原色,如此鮮明對比更能引人注意。那些對生活一點實質幫助也沒有的冷知識,張先生總是記得比誰都清楚。
張先生走進中庭瞧見人群簇擁著一名警察。
「張先生,你們那五樓之一的空姐出事了,兇殺,怪可怕的。「二樓的洪太太看見他,憂心忡忡地說著,咧著嘴,臉頰肌肉隱約地抖動,像一種笑意。
「張先生嗎?」那警察將頭轉向他,問他是否認識五樓之一的蘇小姐,星期三凌晨一點是否在家、是否聽見有人爭吵,看見可疑的人進出?群眾目光全都轉到他這邊來了,張先生低下頭,怪不好意思的。「不算認識吧,就是在電梯碰上會點個頭。」「是的,我在,可我睡了,並沒有聽見什麼。」
張先生有問有答,回話的時候腦中卻浮現出蘇小姐的臉。
一回下班回家他鑽出捷運站不巧碰上一場雨,他撐傘站路口等紅綠燈,一名女孩靠到傘的邊緣來,他轉頭發現是蘇小姐,他們如同在電梯相遇那樣略略點頭。
「好端端的,就下起雨來了。」女孩說。
「欸。」張先生搭腔。
兩人挨在傘下,靜待綠燈轉亮。他暗暗將傘挪過去,肩膀暴露在黏答答的雨水中。綠燈亮了,蘇小姐側過頭對他說謝謝,然後用手掌護住額頭,疾疾奔走起來,張先生見狀便大踏步向前與她並肩。
「哎呀,不用了,」蘇小姐笑說:「雨不大,馬上就到了。「蘇小姐額頭、頭髮全是雨水,語畢,又鑽進雨中。張先生手上的傘撐著不是,不撐也不是,索性收起來,亦步亦趨陪她淋了一路的雨。
蘇小姐腳踩一雙長筒及膝的紅雨靴,張先生注意到她似乎很愛那雙靴子。在另一個晴朗日子裡他與張太太在電梯遇見她。牛仔褲、棉格襯衫和那雙紅雨靴。他背地裡與張太太議論這女的大熱天也穿雨靴,真怪。張太太笑出聲來,「那是威靈頓靴,一雙要四、五千塊,戴安娜王妃、林青霞、凱特摩絲都穿的,什麼雨靴?!你太可笑了。」
張先生心不在焉地想著往事,他悄悄地退出人群,並開信箱取信。走到電梯門口,眼看電梯門正要閔上,並步上前按了開關鑽進去。裡頭站著住三樓的王太太和四歲的男孩融融、住四樓的老婦人,抿著嘴像埃及獅身人面像般嚴厲,身後的印傭懷抱紅色貴賓犬。他低頭說聲不好意思,見門閔上了,又徐徐敞開,一個穿西裝的中年男子站在門口,那是四樓的另一個住戶。那人愣了一下,然後說:「喔,你們先上去好了。」
電梯門閔上。「媽媽、媽媽,那個叔叔最討厭狗了。」融融說。王太太摸著融融的頭要他不要亂說。「真的啦,」融融不甘寂寞地念起童謠,「星期一猴子穿新衣,星期二猴子肚子餓,星期三猴子去爬山,星期四猴子去考試…」融融抬起頭對王太太說:「媽媽,媽媽,今天猴子要考試啦。」
今天星期四。
張先生來到家門口,見對門已拉起黃色封鎖線。他掏鑰匙開門進屋,第一件事即打開電視轉新聞台,他轉身擱下鑰匙和公事包,脫襯衫西裝褲換運動短褲,「新北市板橋區前晚發生一起離奇死亡案件,一名三十歲的蘇姓空姐今早被發現陳屍家中,背部、胸前有多處刀傷。鑑識人員表示,蘇女橫躺在大門邊,然而令人費解的是餐桌擺著鮮花、燭台和紅酒,並無打鬥的跡象,且大門門鏈鎖上,形成推理小說那樣的密室,究竟是他殺還是自殺,有待警方進一步釐清。據了解蘇姓空姐一個人自住,家人多在國外,只有一個妹妹住在新竹。因為週三出勤未到,公司聯絡空姊妹妹,妹妹來到空姐住處,發現大門反鎖,找了鎖匠鉸斷門鏈,才發現死者躺在血泊中,研判死亡時間約週三凌晨一點到兩點左右……」張先生聽著新聞,腦中冒出一段鋼琴旋律,那旋律相當熟悉,但他再怎麼努力也想不起來那是什麼。
他帶著那段鋼琴旋律打開了冰箱,一個個樂扣保鮮盒堆疊在一塊,全出自張太太的手筆。張太太在報社當編輯,下午三點到公司。她中午煮好飯菜約莫兩點鐘出門,回家大約是半夜十二點,因就寢、起床時間不同,和張先生分房睡覺。作息不同的兩個人基本上在一個屋簷下各過各的生活。
張先生獨自吃飯洗碗看電視倒垃圾,日子和其他的日子相較沒什麼兩樣,可今天不同,今天他家隔壁死了一個人。他躺在沙發上,一邊讀《郵政法考前猜題》,一邊在各節的整點新聞溫習懸案的種種細節。
半夜十二點張太太回家,他對張太太說隔壁那個空姐死了。
張太太說她知道,她晚上還處理到這個版面。她說張先生出門沒多久,電視台記者警察全來了。張太太說著說著便岔開話題她說她星期六放假要回鬥六一趟,她外公失智愈來愈嚴重,連舅舅也不認得了。她星期五一下班就搭夜車回去,星期日早上從鬥六回來就直接進報社上班。張先生問是否要陪回去,她說不用。她走進浴室盥洗,然後隔著門呼喊:「過一陣子再去跟房東殺價,先前姿態擺這樣高,現在好了,房子旁死了個人,沒準還能多砍一成。」
張先生與她道過晚安然後回房。他躺在床上,可是一點也睡不著,他如同喝了咖啡那樣亢奮,太陽穴隱約有什麼跳動著。時間也許過了一個小時,也許還要更久,他懶得看表,不知道。他起身到廚房喝水,張太太看完電視早已回房入睡。家裡一片安靜,冰箱壓縮機嗡嗡作響。樓上住戶似乎有人剛洗過澡,天花板上嘩啦啦的水聲沿著排水管往下竄。他腦海中突然又冒出那段旋律。
蕭邦.《夜曲》第九號第二首。
他想起來了,蘇小姐被殺的那天晚上,他聽見牆壁對面傳來蕭邦的《夜曲》。新聞中一個一個的關鍵字如琴聲一樣迸發出來:紅酒。刀傷。門鏈。他們兩戶人家空間格局是一樣的,客廳挨著客廳,浴室貼著浴室,生活像鏡子一樣清楚地對映著。黑鍵。白鍵。黑鍵。白鍵。他閉上眼睛,在黑暗中看見那個女人端著紅酒杯以行板的速度在屋裡走動著,她在悠揚而恬靜的旋律中被刺了好幾刀,每個音符都沾滿了鮮血。
張先生悄悄地走到門口,掛上門鏈,便製造了一個密室。「刀傷穿過肋骨,直達心臟冠狀動脈,大量出血壓破心臟,引起心包膜填塞……」他想起新聞報導中的內容,那多像是推理小說中常見的字句,而如今他也活在一本殺人小說裡了…
星期五,猴子去跳舞
張先生整夜沒睡好,但隔日仍精神奕奕地到出版社去。早上九點半他準時進公司,在自己的位置坐下,扭開檯燈就是一個漫漫長日。聯絡作者確認進度、填印版單、跟國家圖書館申請ISBN、叫紙繁瑣的廬務日復一日,但今天有些小小的變動。他快快把手邊的事做完利用空檔悉心地閱讀空姐兇殺案的網路新聞訊息舖天蓋地而來,空姐的三圍、情史、博客,上過綜藝節目素人正妹卸妝的YouTube都被起了底,簡直跟抄家一樣。張先生心想,人在斷氣中結束生命,可在殺人小說裡,故事卻在人死之後才開始。報紙說警方調閱大樓電梯、前後門和停車場監視器錄影帶,發現並無可疑人士進出,若非自殺就是大樓內住戶所為。換言之,那是密室殺人,雙重的密室。他打開Word檔,在電腦上打了幾個字。
一樓:管理員先生。
二樓:洪太太一家人;二樓之一:一對gay couple?
三樓:王太太、融融一家人;三樓之一:?四樓:怕狗的男人;四樓之一:楊老太太和她的印傭
五樓:張先生張太太;五樓之一:蘇小姐。
六樓、六樓之一:?
七樓:攝影師;七樓之一:?
八樓、八樓之一:?
電腦上的問號其實他也不知道這些鄰居是誰。鄰人的臉都像英文生字,看起來既眼熟又陌生,期期艾艾念不出來。他坐在辦公室椅子向後滑開,凝視著電腦,嫌犯就在名單當中了。他看著這份名單,非常雀躍,彷彿那些字句可以組成一篇小說。他腦海出現了一個句子,「張先生向來循規蹈矩,人生之中最大的罪過不過是在圖書館借來的書上畫線,然而下班回家在自家公寓大樓門口看見警車,心臟還是勐烈地跳動起來......”
年輕時創作的熱情又回來了。
張先生年輕的時候寫過一些小說,在BBS亦好發尖銳文學意見與人筆戰,但張先生後來發現自己資質不過平庸,文字魔力又沒有強大到足以掩飾人生經驗的匱乏,不過認清這一點也沒有什麼壞處,至少不用在文學獎季節開獎時忍受一遍又一遍的失望。而他也犯不著因為讀懂幾本羅蘭·巴特、米蘭·昆德拉,就必須追求與鄰居那一班三姑六婆不同的價值觀。
此時此刻他非常亢奮,他從椅子上站起來,走了幾步又坐下來。連女主角的個性、個性都是現成的,擺在那兒等他抄襲。他點進了她的博客,首頁是她在一盤義大利面前支頤微笑。網頁文章大多描述她在國外買來的包包香水戰利品,也開放代購。
她在自我介紹的欄位上寫著:「一百分的男人難找,不如找十個十分的湊齊一百分,套句松嶋菜菜子在《大和拜金女》的話:接吻只有兩種,一種是和有錢人的接吻,另一種是和窮人的接吻。沒有錢的男人,管他是死是活,我都當他不存在。我的人生不是餐廳、客廳就是咖啡廳。姊妹們,一起享樂吧。」
空姐的博客就叫做“三廳電影”
美麗、拜金,這女人完全符合推理小說的刻板想像,臉上根本寫著屍體或兇手兩個字。張先生心想如果這女人落在阿嘉莎·克莉絲蒂手上,她會怎麼死?如果是瑞蒙·錢德勒,他又會如何透過菲利普·馬羅的嘴,奚落這一切?說說宮部美幸吧,這個日本大嬸應該會對這一切有更溫暖的解釋。
張先生想到一個節骨眼上卡住了,起身上廁所,看見社長先他一步走了進去,於是調頭走往茶水間,裡頭有嘩啦啦的笑聲,幾名編偶像寫真集減肥書的同事躲裡面像在講什麼八卦,看見他進來,噤了聲,張先生倒了一杯茶離開,然後聽見背後炸起嘩啦啦的笑聲。這些年紀小他近一輪的同事沒有排擠他的意思,他們只是與張先生不搭嘎。張先生並非食古不化的人,他用臉書,也會對朋友轉貼堵爛時局的文章按讚。他甚至知道綜藝節目上那些長得像路人,歌聲卻無比嘹亮的人是出自哪個歌唱節目、哪一屆的。然而他比較像是海外僑民,隔海接收故鄉的一切。他們是另外一國的,已婚者之國。可是張太太肌腺瘤難受孕,婚姻八年沒有小孩,與社長、總編們那些繞著孩子打轉的婚姻生活又不盡相同,他們比較像新移民,被陌生的風俗包圍著,所到之處都是他鄉異國。
下午六點半下班時間一到,辦公室的同事有相約看電影,有要去跳佛朗明哥舞的,也有吆喝著去吃麻辣火鍋,有人客套地問他去不去。他笑著搖搖頭,孤立於所有飯局、派對、約會之外,晚上七點準時回家。
上樓前開信箱,電話水費帳單、大潤髮折價印花、寵物旅館的傳單、燙金雪銅紙的春夏女裝型錄。扁薄寒酸的帳單是他的,華麗厚重的服裝型錄是蘇小姐的。他住在五樓,蘇小姐是五樓之一,鄰居的信件總是投到他的信箱來。
他握著百貨公司VIP之夜封館派對手冊,護照尺寸大小,刷刷翻過,香奈兒羽毛珠寶腕錶LOEWE限量鱷魚皮手袋、CHAUMET藍寶冠冕,種種奢華物件在紙面上發光,請帖藤蔓一樣捲曲的英文,如某個異國簽證上的字體允諾一個他們無法企及的遠方。
來到電梯門口,一名白衣黑裙的高中女生站在那兒,津津有味地啃著一隻蘋果,張先生不動聲色地盯著那蘋果上的齒痕和唾沫。兩個穿著同樣款式背心短褲的短髮男子牽著一隻柴犬從外頭走進來,張先生彷彿乾了什麼壞事被看穿一樣,心虛地避開這些人,走樓梯回家。
他一階一階往上爬,大樓裡每一家門戶都長一個樣,然而樓梯間洩漏的遠比自己想像得還要多:二樓洪太太家門口鞋櫃胡亂地塞著花花綠綠的女鞋,男鞋就是那麼一千零一雙,乾癟癟、灰撲撲的阿瘦皮鞋。二樓另一戶住戶則是剛剛看見兩名牽狗的男子,那門口自端午節掛上去的艾草並未取下,每天晚上最誘人的飯菜香總是由這戶人家傳出來。
三樓樓梯間停著一輛兒童三輪車應當是王太太家小朋友的,一個燒金桶似乎是這一、兩日新擺上的,之前沒見過。四樓老太太的印傭偷偷跑到三樓來,坐在階梯上窸窸窣窣用他聽不懂的語言講手機,哀戚聲調彷彿在抱怨著什麼。四樓另一戶怕狗的男人屋內電視開得很大聲像在收看《海賊王》一樣的卡通,嘩啦嘩啦的笑聲當中,隱約有人爭吵,“你講道理一點好嗎?!”一個女人的聲音這樣說,卡通人物格鬥的吆喝聲蓋過了男人的回答。張先生在半夜偶爾聽見這對男女自樓下傳來的爭執。兩人感情似乎很差,但張先生每天早上又會看見這對男女一起出門,女的瘦瘦小小的,但總能輕易地挪開擋住自己去路的重型機車,女的騎機車載男的出門,這男的不但怕狗,還不會騎機車。
他們公寓和所有的公寓沒有兩樣,這些夫妻和其他的夫妻也沒有什麼兩樣,但現在死了一個人,每個人都有嫌疑。身處在一本殺人小說他必須精確地繞過真相,胡亂地揣測幾個人,消耗多餘的篇幅。
星期六,猴子去鬥六
星期六張太太一早就去了鬥六,張先生睡到十點起床,到樓下閱覽室看報。他巡視一遍閱覽室書架上的刊物,《漢聲小百科》、《公寓導遊》、《奧修傳記》、《地獄遊記》....他印像中這架上似乎有克莉絲蒂的《東方快車謀殺案》和《羅傑·艾克洛命案》,突然就不見了。四歲的融融坐在沙發上安靜地畫畫,王太太、洪太太併幾個鄰居聚在那邊議論命案的最新進度。
一群女人誇洪太太昨天出現在電視新聞裡很上鏡。「呵呵,」洪太太自覺地摸摸自己的頭髮,說:「根本是老太婆啦。「他一邊看報紙,一邊竊聽這些女人的對話,張先生有一種錯覺,好像死了一個人,讓大家的感情都熱絡起來。空氣中瀰漫一種節慶的氣味,眾人義憤填膺地講蘇小姐的點點滴滴。她們無私地分享蘇小姐的每一則八卦,言談中有抓奸的憤慨,但也間接得到了通奸的快樂。
張先生岔出心神聽著,突然有人拉拉他的袖子,他回過頭,融融仰著頭看著他。「叔叔給你,」融融把畫畫遞給他:「張阿姨,我畫的。」張先生有異地說謝謝,接過畫一看,血倏地衝上腦門,學生頭、黑鏡框,那是他太太的模樣沒錯,那雙蘇小姐的紅雨靴卻穿在他太太的腳上。他的耳朵一陣熱辣,全是轟轟然的耳鳴。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他接過畫,點頭告退上樓。一進門蹲下打開鞋櫃沒找到那雙鞋,旋即又到張太太房間打開衣櫃,薰衣草香氣撲鼻而來,櫃子上頭擱著幾個紙袋,打開其中一隻,就看見那雙威靈頓紅靴。
那鞋、那衣櫃的東西他全不認得:乾洗過後套著塑膠套的大衣,喊不出名堂的布綢絲棉,他全沒看張太太穿過。拉開抽屜,看著那些疊得整整齊齊的內褲,棉質的、蕾絲的,那感覺異樣又熟悉,感覺上回在床上折騰已經是很遙遠的往事。結婚八年,性變得像倒車入庫一樣理所當然無趣。他帶著懷念的心情把內褲攤在床上,掌心感受那柔柔的觸感,突然間一股熱意自胯下傳來,一顛一顛的。
他溫柔地剝除女孩的內褲如同剝一瓣柚子乳白色的薄膜。掰開了就是滿手的汁水淋漓和晶瑩的果肉。
全都回來了,年幼時的荒唐回憶,以及生勐的性慾。
柚子有時是研究所同學,有時是大學部學妹,那時他念碩二,週旋在不同的女孩之間。他有個從大二就在一起的女友,有一天在圖書館讀書的時候,他發現大學部的學妹把圖書館借書清單夾在他的字典裡,《我坐在琵卓河畔,哭泣》、《在德黑蘭讀羅莉塔》、《想說就會說的表達力》、《你的桶子有多滿》。最初不明就裡,但他後來把書名首字連結起來,
“我在想你”,一切都有了意義。
此後,他輪流帶著女孩們去雜誌上介紹的餐廳吃飯,在蔡健雅、孫燕姿的MV場景擁抱和接吻,年輕人的道德觀跟交通規則一樣,隨時都可以打破。三個人戀情持續到他當兵,學妹跑去女友面前謊稱她懷孕了,用計逼退了女友。但他知道了也沒多說什麼,他只是緊緊抱著學妹,揉著她的頭髮說她怎麼這麼笨。那時候,人生多美好,前程遠大,一晚好幾次。但現在回想起來,那已經是他人生的巔峰了。
他預計當完兵去英國讀書,退伍後申請學校的空檔有個出版社找他去上班,第一年操盤的書就得了獎,整個人誌得意滿。第二年因母喪沖喜,他很快就和學妹結婚,出國的事也就耽擱。家裡本來給他預備了買房子的頭期款,可父親經商失利,所有的錢都填上,他和學妹在外面租房子,兩人生活以存錢為最高目標。他們不到外面吃飯、不看首輪電影,也不在家宴客。學妹變成張太太,突然什麼都有了算計。婚前她早上會貼心地幫他擠好牙膏,婚後她開始指責他牙膏總是從中間擠。他用完廁所總是不隨手關燈、洗衣服的時候洗衣粉倒太多、冰箱的剩菜沒用保鮮膜包好,他們在日常的細節中爭執,在爭執中改變。他開始困惑,婚前兩個人各賺各的,生活很有餘裕,何以結婚了兩份薪水反倒不夠用?
後來,張太太到報社工作,兩人錯開作息,一天說不上幾句話。偶爾碰上在家一起看DVD兩個人窩在一張沙發上,以往如同兩隻湯匙完美地疊一整夜也不覺得累,但如今擁抱著,他僅能聽見衣服與衣服的摩擦,骨骼與骨骼的碰撞,那一聲嘆息。
婚後他和別的女人上過床,有一年他到北京參加書展,飯店櫃檯有電話打來問要不要叫小姐,說有個吉林來的像Jolin的女孩,很清純。
他的道德、理智、身體的每一個毛細孔都在喊“不要”,可喉嚨吐出來的聲音卻是“好”。
女孩上樓來了,哪裡像Jolin,那根本是《全民大悶鍋》裡戴假髮的九孔。張先生不懂拒絕,和那女人狼狽地接吻,零錢還從口袋滾落。嚴格說起來,那背叛其實短短一分鐘不到,他覺得那沒什麼,那個妓女就併著擦拭過精液的衛生紙被丟到馬桶沖掉。他沒有任何情緒,只要他想隱瞞,他就可以一輩子瞞下去。
他盯著那內褲,腦中萬念紛飛,如此一個敢愛敢恨的女孩被他愛得這樣平凡,愛成......一個嫌疑犯?他盯著紙袋,彷彿那是一盤填字遊戲,可以藉由紅鞋填滿妻子與殺人犯之間的空白格。
他的視線轉到牆壁上去,想起剛搬來這房子的那一天,那兩房一廳的房子空蕩蕩的,他和新婚的妻子商議著床要擺哪裡,書架要放哪裡,他與新婚的妻子在空屋中快樂地打轉,突然就勃起了。空房間讓他亢奮,他把妻子推到牆上狠狠地吻著。新漆的牆壁雪白如稿紙,彷彿可以寫下任何字,什麼都有可能,可是轉眼之間就剝落髒污了。
星期七,猴子刷油漆
隔日,張先生去買了刮刀滾桶油漆,帶著懷念的心情把客廳刷過一遍。期間有刑事大隊的人來問話,他意態闌珊地回答。刷白了一面牆就過了一天。深夜,張太太回家看了新漆的牆,愣了一下,但也沒多說什麼,她只是坐在沙發上稀哩唿嚕地吃著肉羹麵。張先生坐在沙發的另一頭看著他的妻子,突然心生一股衝動,想伸手將她攬過來,對她坦承那些餐桌上的緘默、那些無法四目相交的心虛,他想對她供出一切,甚至包含北京的那次買春,但他坐得太遠,手太短根本夠不著。「明天記得繳瓦斯費。「張太太吃完面,洗澡,與他互道晚安,然後進房間。
他一個人在客廳。不開燈的房間,狹小如公車車廂,他是周日的末班公車唯一的乘客。
早上他上班,張太太還在睡覺,他與他的妻子似乎只剩下晚安可以說了。蕭邦的旋律又浮現腦海,他閃過了一個念頭:「出門的時候,妻子真的在房間睡覺嗎?」黑鍵。白鍵。黑鍵。白鍵。視線穿過白牆,他看見相關人等鉸斷了門鏈,進了門,看到屍體,驚慌的驚慌,報案的報案,全亂成了一團。以常理推斷,應該沒有人會在這個當下冷靜地將整個房子巡視過一遍吧。假使兇手本來就一直藏匿在房間裡呢?黑鍵。白鍵。黑鍵。白鍵。張太太在蕭邦的旋律中優雅地從蘇小姐的床底或衣櫃走出來,那混亂之中,一個好奇關心的鄰居出現現場完全合情合理。
就這樣,張先生解開了密室的謎。他低下頭,心裡就有了盤算。
星期一,猴子穿新衣
星期一上午八點半,張先生離開家搭捷運去上班。到了辦公室那一站,他仍鎮定地坐在椅子上,他在車廂裡傳了簡訊進公司,說拉肚子不進去了。他在離電影城最近的車站下車,看了場早場電影,然後走進一家牛仔褲服飾店。張先生婚後少買衣服,走進流行服飾店家,竟心生一種異樣的怯意。反摺褲、垮褲、AB褲.....那些不同款式的名稱疏離得像是學術用語,他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指著海報上穿著帽T垮褲,眼歪嘴斜的陳冠希說:「給我一模一樣的衣服和褲子。」
別扭,又把褲頭往上提,提到中年人的位置。面對鏡子,帽T垮褲,他是穿著嘻哈裝的菲利普馬羅。
他在更衣室換了衣服。褲子鬆垮垮的,褲子如同土石流鬆動一路滑下,滑到離青春比較接近一點的位置,半截內褲都露出來了。他覺得很下午一點鐘,他穿著新衣服回到自家公寓對面的簡餐店。點了紅茶,盯著窗外漫不經心地翻雜誌。兩點鐘。蘇小姐從大樓走出來,墨鏡,格子衫牛仔褲,紅色威靈頓靴,喔,不,那不是蘇小姐,那是張太太。他快快結帳跟著出去,他低著頭盯著那紅靴子。紅靴子上了捷運,紅靴子下了捷運,紅靴子往報社相反的方向走去,來到了一家百貨公司。
張太太摘下墨鏡,在百貨公司門口,俯下身盯著玻璃櫥窗一雙麂皮涼鞋許久,然後優雅地走進了一家名牌服飾店。
他透過櫥窗望進去,均勻的光線撒滿整個空間,張太太在裡面如同逛美術館那樣緩緩地移動,旁邊亦步亦趨跟著西裝畢挺的俊美男孩,臉上掛著洗練的微笑,張太太在更衣室換了一件新洋裝走出來,她在鏡子麵前比畫著,男孩不知在她耳邊說了什麼,張太太就笑了。她換下衣服交給男孩,走到櫃台結了帳。
張太太拿著提袋走出了服飾店。他遠距離低頭盯著那紅靴子,紅靴子走進另一家珠寶店,不到十分鐘又走出來。紅靴子突然停下來。張太太一個轉身,他來不及躲避,視線就撞在一塊了。
兩個人都愣了一下。
「你在這裡幹嘛?」張太太問。「你在這裡幹嘛?」張先生反問。
「買衣服。她說今天是百貨公司的Family Sale,她請假來買衣服。她拷貝蘇小姐的穿著,拿著蘇小姐的邀約卡買折扣品。
她變成蘇小姐,偷偷模仿另一個女人的生活,那就是她的罪行。
「幹嘛這樣偷偷摸摸的?」張先生問。
她說:「沒有一個女人抄襲另外一個女人的穿著會想讓人知道,好嗎。」
他腦海閃過融融的童謠,他說:「星期一猴子穿新衣。」
張太太蛤一聲問他說什麼。
他說:“你記得猴子的童謠吧,就是星期一猴子穿新衣那個?!”
他們順勢在百貨公司中庭的音樂噴泉邊緣坐下,張太太把童謠念了一遍。「星期一猴子穿新衣,星期二猴子肚子餓。星期三猴子去爬山。星期四猴子去考試。星期五猴子去跳舞。星期六猴子去鬥六。星期七猴子刷油漆。星期八猴子吹喇叭。星期九猴子去喝酒。星期十猴子死翹翹。」
他說:「你不覺得這隻猴子很虛榮嗎,一個星期的開始就把錢都花在新衣服上,肚子餓,要考試了書也不好好念,前一天還去爬山,成天玩樂酗酒,然後就死掉了。」
「所以這是一隻虛榮的猴子,過勞死掉的故事?」張太太問。
他點點頭,回答:「所以這是一隻虛榮的猴子,過勞死掉的故事。」
張太太打了他一拳說,「你罵我猴子就是了。」張太太反問他何以穿得這樣怪模怪樣。他盯著玻璃窗內的菲利普·馬羅,說出了這幾天內心的百轉千迴。他說出了他的推理,說他誤以為張太太是兇手,除了北京買春的事,他什麼都說了。張太太聽完翻了一下白眼,罵他有病,但嘴巴掛著笑。
「那我的行兇的動機是什麼?」張太太問。他遲疑了一下,撓撓頭然後說:「殺了鄰居,讓公寓變成兇宅,然後讓房價下跌吧。」
「那是真的喔,我昨天在公司上網查了一下,兇宅真的比一般房價便宜兩成到五成呦。」張太太說。
一名推著嬰兒車的女子從他們面前走過,車裡探出一個狗頭,她說:「這年頭嬰兒車上面坐著的多半是狗。」張先生像是被這話蜇到,身體抖了一下。「酷卡,那疊邀請卡,快,你帶出來沒有?裡面有一張寵物旅館傳單,快,蘇小姐有養一隻狗對吧!」張太太不解地從包包取出傳單,他按上面的電話打過去說自己是蘇小姐的朋友,詢問蘇小姐有沒有狗寄放在這裡?電話那頭答:「哎呀,我們看了新聞很傷心說,想說菲菲不知道該怎麼辦?她星期二傍晚把菲菲送過來,誰知晚上就出事了,多漂亮的一個女孩子....「張先生沒等對方說完就把電話掛了。
「她在被殺害的當晚把狗送去寵物旅館,」他拉高音量對張太太說:「可她在家和人喝酒,這不合理,唯一的解釋是與她喝酒的那個人怕狗。「所有的謎底已經揭曉,填字遊戲的空格已經填上,他幾乎是用喊的喊出那個名字。
怕狗的男人。
張先生說:「完全密室殺人是不可能的,殺人行兇掛上門鏈然後逃逸根本辦不到,但假使門鍊是被害者掛上的呢?假使兇手殺人根本沒有檢查被害者是否斷氣,然後慌張逃開,假使被害者最後一口氣不是用來求救,而是把門鏈掛上…..”
電視上的記者說自稱死者鄰居的周姓男子稍早到警局自首,坦承犯案。他與蘇小姐是大學時代的戀人,婚後搬到目前所住新家才發現蘇小姐是樓上鄰居,兩人再續前緣。他欲與妻子離婚和蘇姓被害人復合,可蘇小姐不肯,兩人爭執,他一時氣不過拿起水果刀刺傷蘇姓被害人。畫面一轉,怕狗的男人與警察回到自家公寓大樓重建犯罪現場,大批記者圍上,閃光燈此起彼落,怕狗的男人突然雙腿一軟掩面哭泣,他說:「她說謊,她說她拜金,她是騙人的,她交男友只是不想讓我為難,有壓力,她在維護我,她到死都在維護我」怕狗的男人發出了像狗一樣的哀鳴,被遺棄的小狗在深夜發出的那種哀鳴。
張太太轉過頭看著張先生,說:「你破案了菲利普‧馬羅。」
時間還早,毫無同情心的兩個人一起逛書店和無印良品。他們在美食街吃了好吃的拉麵,甚至在湯姆熊逗留一會兒,玩了一回射擊遊戲。因為張先生今天是菲利普·馬羅,所以分數很高。
他們搭捷運回家,他望著對面車窗上他與妻子的身影,玩累了的蘇小姐依偎在菲利普,馬羅的肩膀睡著了,眼皮微微跳動,睡得很熟。如果在殺人小說裡,他希望小說在這個句子結束:「他們家隔壁死了一個人,他們從此過著快樂幸福的日子。」
快到家了,他遠遠看著停在家門口的警車正要開走。他沒來由地想起有一次小學遠足他睡過頭,父親騎機車載他到學校,可趕到校門口遊覽車已經開得遠遠的了。錯過了在動物園散步、錯過了參觀汽水工廠、錯過車上和同學分享零食打電動,想到自己已經錯過一個歡樂假期,他委曲地啜泣起來。父親甩了他一巴掌要他不准哭,於是他哭得更大聲了。
警車如遊覽車消失在路的盡頭,他想起往事,此時的心情大致如此。人生並非殺人小說,他的假期到底是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