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時光留聲》原著小說介紹
今天要給大家推薦的同樣是一部《時光留聲》,該劇演員顏值和演技也是相當的不錯,尤其是電影《時光留聲》原著小說介紹關於這個話題相信大家也是充滿了疑惑,就讓小編帶大家一起來看看。希望看完的朋友喜歡這篇文章。
電影《時光留聲》原著小說叫:《The History of Sound》(Ben Shattu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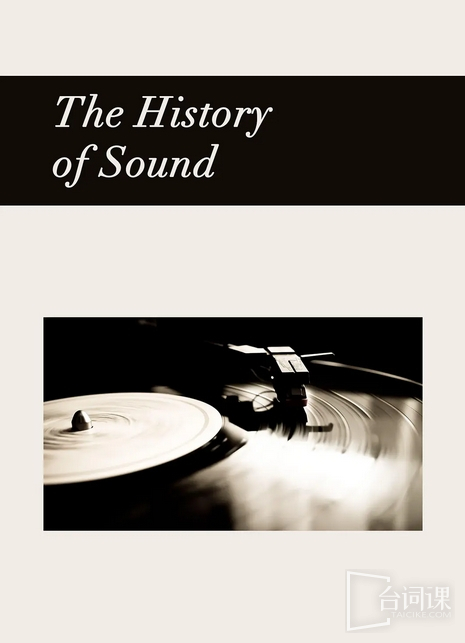
《時光留聲》原著小說講述一戰時期兩位音樂專業的年輕男子,他們相約穿越美國,記錄下他們美國同胞的生活、聲音和音樂,在途中他們也發生了深刻的改變。
電影《時光留聲》原著小說節選
我遇見大衛時,我17歲,那是1916年。而現在已經是1972年四月了,年紀什麼的對我來說早已沒什麼意義。在我書桌上方的窗戶上,總是漂浮著一些白色的泡泡絨球,應該是某種植物的種子莢吧,它們沉積在劍橋的人行道上,就像是剛下過一場初雪。
醫生建議我寫下這個故事。當我收到一個來自緬因州的陌生包裹後,我就一直失眠。包裹裡有25個蠟質留聲機圓筒,每一個圓筒上面都貼著一個標籤,上面都寫著我和大衛的名字,在其中的一個圓筒上,貼著一張紙條:「幾年前,我在閣樓中發現了這些,當我在電視上看到你時,我就知道,這些一定是你的。「我寫了三本關於美國民俗音樂的書,它們反應都不錯,因為我最近做了很多訪問。(想必他就是在這些訪問中看到我的吧。)時至今日,我都沒有寫過那個夏天的事,那個關於大衛的故事。而現在,我想,是時候了。
我第一次遇見他,是在秋天。在新英格蘭音樂學院第一學期考試後,我和馬特,還有勞倫斯一起到酒吧慶祝。而大衛就在對面遠處牆邊彈鋼琴,在昏黃的燈光下,他白色的襯衫看起來也有些發黃,他的雙臂在琴鍵上輕輕掃過時,他的肩膀鬆弛而又舒緩。
「你在想什麼?」馬特輕輕敲了敲我的肩膀問。
我沒有註意到他在說什麼。
「你在盯著看什麼?」馬特轉身又繼續問。
「我知道這個曲子」我說:「《死寂冬夜》,在肯塔基州,我的父親曾經用小提琴演奏過這個曲子,曲調很慢,我父親說,他的節奏就像「一個靜坐之人的呼吸」。它是一首來自湖區的古老的英國民謠,我曾經研究過它。它講述了兩個戀人,在一月的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走散的故事。
他們從各自家中逃跑,相約私奔,約好在一棵橡樹下相見,但是暴風雪來臨了,他們在雪虐風饕中呼喊彼此的名字,但是無濟於事,聲音淹沒在暴風雪的嗚嗚怒吼中,根本無法聽到彼此的聲音。最後,他們蜷縮在不同的樹下,孤獨的死去:「在雪地上,有兩條足跡顯現出來,一條向西離去,一條向東延伸,兩個靜止的身影,在樹根上,在這個死寂的冬夜裡,永遠不會相遇。」
一想到這些,我就會回想起,在肯塔基州的夏天,白蛾在門廊的周圍飛來飛去,我和弟弟仰面躺著,雙手放在腹部,感受著父親腳下傳來的緩慢節奏———他的靴子與木板交錯聲。而樹上的蟈蟈,將整個黑夜融合。
「離開一下」我對馬特和勞倫斯說到。
我朝著音樂的方向,穿過人群。在房間裡,充滿肥皂、啤酒和菸草味,我靠在牆上,臀部觸摸在鋼琴的尾部,看著大衛彈奏。他閉著雙眼,口中的香菸已經快要熄滅,煙霧在他臉上緩緩升起黑色的頭髮朝後背梳去,他的頭隨著合唱團而律動,我注視著他的身影。
「你是從哪裡學的?」當歌曲結束時,我向他問道。
「噢」他將煙都在地上,然後抬頭說:「在肯塔基州的湖區」。
一個很低沉的聲音,語速很快。他用一隻手彈了C和弦,另一隻手從地板上舉起了酒杯。
“我來自肯塔基州”我告訴他。
他的手觸碰著琴鍵,有又一次抬起頭看說:「嗯。你果然是來自肯塔基州的,不好意思,我是大衛」。他伸出手說。
「里昂」。我說。
「你是哪個學院的?」在酒吧的那個夜晚,基本上每個人都來自音樂學院。
“聲樂部”,我回答。
「不錯」他說:「Fa——La———La,我是音樂歷史學院的,這個———」他又演奏了一次相同的旋律。「就只是一個愛好。在夏天的時候,可以獲得一些靈感」。
在房間的另一側,馬特和勞倫斯示意我要離開了,我向他們揮手道別。
「你去過哈羅嗎?」我說:「我在哪裡長大」。
「哈羅,兩年前去過,那時是夏天,我記得在市中心有一個天藍色的涼亭。」
他似乎並沒有驚訝於這種巧合,同樣的,我也沒有。在那時,音樂學院中來自南方的人並不多,更別說來自哈羅的了。哈羅是一個位於冷河和莊嚴河之間的一個兩千多人的小鎮。大衛去過那裡,也許我們甚至見過彼此。在我記憶中的某些時刻,無比的懷戀家鄉。
「我曾經在那裡學過裡爾舞曲,」他說,「我想應該是《Maids of Killary》。」
“我知道它,那你也應該知道《Seed of the Plough》了?”
「我應該知道嗎?」他說。
我和他說,那是我母親常唱的歌。
「來吧,讓我也聽聽」。
「不了」我使勁的搖頭。
「什麼調?」他說著便在鋼琴上彈了起來,從一個和弦到另一個和弦,接著他又往前坐了坐。「什麼調?」他又問了一遍。彈了一個A調。
他的眉毛隨即揚了起來,我注意到他的上嘴唇有一道淡紅色的疤痕,我後來才知道,那是來自於他的父親。
“你別以為你能彈出它來”,我說。
“這舞台是你的了”,他推開了琴鍵,從口袋中取出了一支煙,並拿起一根蠟燭,火焰在他的臉上搖曳,他靜靜等待。
我第一次被告知有絕對音感,那是因為我能夠準確地辨識出母親每日清晨咳嗽聲的音調。我可以和穿過田野間的犬吠聲完美和音。我還是父親小提琴的調音器,我站在他的肘邊,當他撥弄琴弦時,唱出A調。一開始,我以為所有人都能感知聲音,像是D調,他就是一個搖擺不定的黑莓色圓圈。我只需要去調整我所看到的形狀,就能準備辨識各個音調。當我13歲時,音調就開始有了味道,父親拉了一個糟糕的B小調時,那麼我嘴里便全是蠟質的苦味。相反,如果拉了一個完美的C調,那麼它嘗起來就像是甜美的殷桃,而D調,則像牛奶。
當時我為大衛唱了那首曲子。
我總是感覺,那不是我唱的。即使聲音是從我的嘴唇和喉嚨發出的,但我總覺得這聲音不屬於我。他更像是我竊取而來的,而並非我本來所有。這具身體的確屬於我──我能感受到我橫膈膜的起伏,聲帶的伸縮,以及我嘴唇和柔軟舌頭發出的聲音。這一切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但是,有某種東西,之於我消失了。聲音是在我頭頂響起的,所以我頭骨的感覺要比肉體的感覺更真實,他淹沒了我耳朵鼓膜,鼻翼的震動。而不再屬於我自己,更像是在樹林中風穿過的聲音或是穿過玻璃杯的聲音。或者說是一個來自於我口中的回音,不斷重複,我無法在那樣唱歌了,我懷戀它。現在我有這樣的微弱的顫音,沒有人告訴我這種嗡嗡聲不好。
當我唱完這首歌時,黃昏漸漸退去,變成了一種濕木的氣味。
“你到底在哪裡學的”,他驚訝地問我。
我聳了聳肩,
「如果我有這樣的嗓音,我肯定不會將他們埋沒在學校」。
當他站起來去拿新啤酒時,我發現他比房間裡任何人都還要高,直到破曉時分,我們都待在一起,我唱歌,而他彈琴。
我可以在兩個八度音階上都哼出D調,但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他這樣有記憶力的人。他抬起頭,一手摀住耳朵,哼著一兩個音符,他輕鬆地唱出這首歌曲,只有當他完全喝醉時,才會笨手笨腳的重複一句歌詞。
“我再買瓶酒給你”,我對他說。在微亮的晨曦中,我從未離開過鋼琴一側。
“好的”,他說:“你讓我一宿味眠,你欠我的”。
“任何你想要的”,我凝視他,輕輕地說。
「不,我累了。現在都快天亮了。我想睡一會兒,我就住在這條街的對面,如果你不嫌棄的話,我那裡還有一張沙發。」
他的房間空到不行,只有一張床,一架鋼琴,一張椅子。根本沒有沙發,甚至沒有桌子,髒盤子和杯子以及一頁頁的音符都散落在地,我向他要了杯水,因為我感覺這間房間在不斷地旋轉,我喝醉了。他從廚房拿了一個杯子,喝了大大的一口,然後向我噴出一段弧線。我張開嘴去接住這些噴灑的水,他一直這樣做,直到杯子空了,而我也濕了,但也喝到了一些,他把杯子丟在地上,然後走向我,摘下我的眼鏡,把它們折起來放在窗台上,他脫掉我濕了的襯衫,並且把我帶到他的床上,有一堆被子和床單,當我附身去吻他的嘴唇時,徑直
了他的嘴唇上的那個淡紅色的疤痕,當他把手壓在我的我的大腿上時,我吸允著他,他跌落在床上,用腿盤繞著我。
當我醒來時,早已天亮,大衛已經離開了。我還是一陣頭疼,整個房間也依舊在旋轉,我之前也喝醉過,但從來沒有像這樣過。我從床上爬起來,在地上看到一張紙條「」下週見」。我從他水台中大口大口的接水喝,然後接了滿滿的一大杯,走進臥室。我躺在靠椅上,一口喝完這杯水,然後又回到床上,蓋上被子。當我再次醒來時,太陽已落山,但他仍未回來。因此我也就穿上衣服,在離開前,我將他留下的紙條,折好放進口袋裡。
那之後的每一個星期二夜晚,大衛都會在鋼琴前抽著一支煙出現在那裡,而我則會用獎學金津貼,請我們喝酒。即使不是星期二的夜晚,我有時也會站在他公寓的面前,抬頭看,試圖去看有誰會出現在他公寓周圍,我告訴自己,這只是出於好奇。我真的從來沒有認為,這是出於嫉妒,在我遇見大衛之後的每一段關係,都存在著這樣的問題。像是克拉麗絲,我40歲時的約會對象,在她承認和我的朋友上床之後,離開了我,但我告訴她,我只是希望她能更早的承認,並且希望可以一起解決它,但是她開始對我大吼大叫,好像出軌的人是我一樣,反正我對她並不在意,為什麼又要留下呢?我曾經交往過的大多數男人———艾利克斯、威廉、艾利斯泰爾以及其他的人,最長的時間都沒有超過幾個月,文特森是最長的一個,我是在羅馬遇見他的,在1929年至1930年之間,我在羅馬差不多一年多,他來自米蘭,機智敏捷。他對我們遇到的每一個陌生人都很有魅力,在他兩顆門牙之間有一道縫隙,他的笑聲迴盪在羅馬的每一條狹小街道中,文特森是一個大提琴手,他會在我唱歌的教會練習。當我因為事業而要回到波士頓時,他只說了一句:“美國佬”,好像這是他能想到的最糟糕的詞。
我並不想詳細訴說大衛離開時的情景,那是1917年,在我與他第一次見面後的一年半之後,美國參戰了。班級被解散了,他也去了歐洲,而
我並沒有去,因為我的眼睛視力很差,在他的日記中,我寫下了在哈囉的地址,告訴他,記得寄法國巧克力給我。
我回到了哈羅,回到農場,去幫助我的弟弟,他在我回來不久之後,也去了歐洲,也許這就是我與大衛最後在一起的日子。在波士頓週二晚上的十幾次約會中,我又以一種年輕的方式想起了他:在清晨,仰躺在床上傾聽鳥兒歌唱,柔軟的床單纏繞在大腿上,當我在廚房靜靜等待水壺中的水燒開,當我對果樹進行修剪、嫁接、立樁和拉線,當我剛下班後,漫步於溪邊,聽到青蛙的叫聲,坐在我們的門廊上,聽著雷暴在地平線處用三個音符清嗓子,在雷雨過後,呼吸泥土的芬芳。一如既往,有時,當我醒來,他的臉龐便會出現在我的眼前,我的手一伸過去便會觸碰到他。我盡力不去想,但是我的身體已經刻下了他的烙印,灰藍色的眼睛,虹膜周圍有一圈棕色的東西,眼皮上的雀斑,嘴唇上的傷疤,喉結像斷骨般明顯,他的頭髮聞起來像菸草,他的脖子像是發酵的水果。我沒有精經歷我那個時代的一些男的會有的罪惡感,我只是愛他而已,僅此而已。我的錯誤在於,我認為大衛是眾多第一次中的一次而已,我嚐到了愛的滋味,我熱切的期待著未來,我怎麼會知道我生命中的其餘人———艾力克斯、威廉、艾利斯泰爾、山姆、克勞利斯、莎拉,還有最近的喬治———在洪水般的第一次後,所有的後來都變成了小溪。
夏天、秋天都已過去。冬天如約而至,並下了一場雪,但不像波士頓那樣。我花了好幾個月,寫了一些糟糕的音樂,還喝了很多咖啡,無數次的散步。幻想著生活會恢復原狀,戰爭會戛然而止,我將會回到北方,回到學院,回到波士頓,而在那裡,我也確信大衛也會服役回來。
有時,我會去探望我的祖父,他住在城郊,在他父親為他和六個兄弟建造的房子。我的父親,早年,便是死在了這裡的果園裡,我的弟弟發現他時,他手裡還拿著剪刀,我的母親也因為這件事,開始散步,有時甚至一直到深夜,我和弟弟都不在,這房子便顯得異常冷清了。我的祖父會坐在爐邊的靠椅上,無論夏天或冬天,都裹著一張毯子,我們喝咖啡,談論著歐洲的戰爭,以及我是否有弟弟的消息,然後他會讓我唱一首歌,但他從來沒有問過我關於音樂學院的事,他不喜歡談論肯塔基州以北的任何地方,他曾在安提坦的騎兵隊服役,看著他的戰友“被肢解”,他並不是一個壞人,他只是氣憤,他失去了他的朋友以及妻子,我現在感到驚訝,僅僅只是寫這篇文章,就有如此多的戰爭向我家庭生活襲來。
在1919年6月,大衛的信到達的農場。回信的地址是緬因州的鮑登學院。它寫在了一張五線譜紙張的背面,正面是兩條四分音節,弧形穿過高音譜號,只有一段話:
我親愛的銀嗓子同盟者:
我希望這封信能寄達給你,你在農場過得如何?就目前來說,我從歐洲北部徒步旅行回來了,上帝保佑啊,但是日子也越來越好了,我在鮑登學院這獲得了一個職位,就在常青樹那裡,上個月,有名男子來參觀了學院並展示了一架新發明的留聲機原型。我的導師認為如果我被選中,在這北方荒野裡,為學院裡錄製民歌那將會很好。我自己無法一個人拖著這台留聲機——今年夏天在樹林裡散步怎麼樣?往北方去,有星空下的松針床,樺樹啤酒!別想了,來吧。
另外———你有錢嗎?在這裡,周圍沒有什麼地方可去的。
我把紙張翻過來,看著我能看出的兩個音節,是一段能觸動我內心的旋律:我從大衛那裡得到的每一封信,最終都變成了一個「指令」:「下週見”,他在第一個清晨寫下的。然後是:「別想了,來吧」。大衛給我指示,是而我就聽從它。
那個夜晚,我躺在床上,將信紙放在我的臉上,我和母親說,我在波士頓得到了份工作,我將會在一周後離開,那時,這農場將沒有人照看,這果園將會雜草叢生,網也將無人鋪設,如果我長時間無法回來的話,這些水果將會熟透,散落在周圍腐爛,但我並不在意,我逃離般的離開,坐上火車,從路易斯維爾到紐約,從紐約到波士頓,再從波士頓到波特蘭。
我從來不太在意那些客觀存在的事物,比如,盤子碎了,幾年前我的家被洗劫了,說實話,我感覺並不糟,我感到麻煩的是支出的問題,我家的牆是完全沒有裝飾的,我要求我的朋友們永遠別給我買聖誕禮物或生日禮物,這可能會被認為是節儉或有意義的,但這在我年輕時,是個問題了。我過去常常丟東西,把外套遺留在了教堂的長椅上,丟掉了課本,在草地上弄掉了一把斧頭,我白送給其他孩子大量的玩具———我父親的松香木小提琴,硬幣。最倒楣的是我家的狗——我在學校喜歡上一個男孩,一天我就帶著小狗去他家,然後把它綁在他家草坪上的一個樹上,回來的時候忘記了,因此我父親還打了我。
我仍然還留著大衛留給我的紙條,那張問我去不去北方的紙條。仍然留有他家地板上留下的紙條,仍然留有某個晚上他遺忘在鋼琴上的剛卷的煙,留有來自於我們相會的地點的火柴盒,我並沒有留下我離開羅馬時,文特森送給我的雕像,或是周年紀念克勞麗斯送我的黃金手錶,或是莎拉為我畫的景觀畫,或是我與艾力克斯在科德角一起收集的海玻璃,但關於大衛的一切,我就會變得像一隻貪得無厭的喜鵲。
站在波特蘭火車站,當他還沒看到我時,我就看到了他,我在不遠處,看著他:他穿著一件亮藍色的T恤和一件深色的夾克,他雙手插在口袋裡,抽著煙。他留了鬍子,看起來更瘦了,臉頰更有棱角了,當他手臂伸過頭頂,我感到了一陣心跳加速,就像一個不知道需要回到原位的器官一樣揮著手,他用手指著我,像一把槍一樣,想我開火。他的周圍全是一些錄音設備。
從1919年八月到九月,我們走了100英里,我們收集了一些民謠和曲調,從岩石海岸到無盡的柱廊森林內部,然後回到海岸。穿過了迷霧沼澤,森林裡響起了青蛙的叫聲,還有差點讓我們滑倒的苔蘚。沿著海道路,那裡的風異常猛烈,幾乎將我們吹倒,我們參觀了小鎮,當然還有花崗岩採石場和農場,在哪,我們聽到比以往更好聽的歌曲,大衛總是介紹我們的那個,而我則是微笑著後退。
我們完成了計劃,某人的表弟可能認識某人在北邊20英里的阿姨,有時我們呆在錄音的房子裡,單更多時候我們會在戶外睡覺,在一個大衛帶著帳篷裡,我就負責搬運錄音機,那是一個晴朗的夜晚──就像那個夏天的夜晚一樣,我們沒有帳篷,就睡在田野間或鬆樹下。我們的四肢因為白天的步行而疲憊不堪,晚上我們就沉沉睡去。
我的祖父曾說:「故事並不意味著幸福」。因此,我並不想過多的敘述剛開始的幾週。雖然沉重的留聲機帶子扎進了我的肩膀,黑蠅在我的脖子上留下了血痕,我的靴子在腳後跟磨起了銀元大小的水泡,但我認為我從來沒有這麼快樂過——以一種平淡、沉悶、修飾性的方式,是無法進一步表達的。他出現在圖像中:當我們穿過被雨打平的海菲爾德時,太陽才從雲層中露出,周圍的雨珠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周圍還有在歌唱的鳥兒。大衛在瀑布下洗澡,然後我們就在巨石上纏綿。當食物吃完了,我們尋找到了藍莓,像是尋找到了一個禮物,整個下午我們都在吃,它既噁心又幸福,因為吃太飽,而無法前進,我們在哪裡午睡,直到一個女人用靴子叫醒醒我們,那個夜晚,在淡紫色的暮色裡,他要我伸舌頭,然後他也把舌頭伸出來給我看,我們都是青紫色的。我想起了哈羅,無人照看的果園,想起了吃果子的鳥兒,想起了果園裡長出的雜草,但我並不在意。
我的工作是操弄機器:將蠟筒從紙皮上拆下來;表面刷乾淨;安裝在旋轉器上;並將喇叭對準歌手的臉,讓他或她沿著管道唱歌;將唱針移到蠟上;慢慢轉動曲柄。錄音完成後,大衛將歌詞和音符轉錄成一本小冊子,並附上一段關於人物和歌曲起源的簡短訪談。我喜歡這些歌曲,但不像大衛那樣喜歡它們。我不知道熱情從何而來──他不是聽著歌長大的,不像我和弟弟。但話又說回來,我對大衛的早年生活知之甚少——每當我問起,他都會搖頭,像拍黑蠅一樣的揮手,說沒什麼好說的。我只知道他出生在紐約,他小時候在倫敦住了幾年,因為他父親的工作——我不知道他的職業是什麼——他在去音樂學院之前搬到了紐波特。他確實曾經提到過英國的一位拉小提琴的叔叔,並帶他去愛爾蘭進行了為期一周的旅行。也許這就是他收藏的起點——現在,六十二歲,我知道我們所愛的大多數東西都是在我們十歲之前播下的。當我問他喜歡這些歌曲的什麼,尤其是民謠時,他說——我清楚地記得他的話——它們是他所知道的最熱血的音樂作品。我明白他的意思,歌曲中充滿了成千上萬歌唱者的聲音並改變了它們,它們始終是人們生活的故事。不像我在音樂學院開始喜歡的巴洛克音樂,尖銳、抽象、華麗,就像是一件冷光閃閃的完美珠寶。民歌柔軟細膩,光是旋律就讓人哽咽。歌曲中的情感;沒有什麼花俏。在我們的收藏之旅結束後的幾年裡,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我不想唱那些老歌。我轉向合唱團音樂,轉向大教堂中的圓弧獨奏,這就是為什麼我在 1929 年在羅馬的合唱團找到了一個職位。直到我五十多歲時嗓子發啞,我才發現我唯一想寫的東西是美國民俗音樂,從歐洲傳入的傳統,不斷綻放和變化成新鮮事。純屬偶然,我的寫作恰逢紐約和波士頓的民謠復興,所以我的書賣得很好。並沒有超越我的理解,我把它們寫成一種對大衛的紀念,但沒有提到他的名字。老實說,我又開始愛上音樂了,我家鄉和整個阿巴拉契亞地區的古老蘇格蘭-愛爾蘭歌曲,以一種我久違的方式。
在 1917 年那個夏天的所有錄音中,我覺得我們錯過了最好的聲音。我想要一份我們工作的音訊日誌。暴風雨從山谷襲來的聲音。松樹枝條從頭頂掠過的聲音。八個孩子的木勺在奧古斯塔以南的一張桌子上敲打著木盤的聲音;劈啪作響的豬油圍繞在煎鍋中燃燒的肉的一側。當我們第一次來到螢火蟲閃爍的田野時,我想記下大衛的低語,「聖潔的耶穌」;一隻鱷龜的爪子在林肯的一張桌子上刮擦;在庫博的序言中,諾拉泰特爾和她的三個女兒都非常渴望將她們的歌曲錄製下來,同時唱著完全不同的歌曲,每個泰特爾都試圖超越其他人,直到大衛不得不將兩個平底鍋子敲在一起讓她們安靜下來。索斯維克的洛夫威廉斯坐在廚房的中央,當我試圖修理留聲機時,唱著調式曲調,她的六個孩子和五個繼子女都安靜地坐在她身邊,直到洛夫唱到第二句副歌,當孩子抑制不住自己,一個個來到媽媽身邊。十二位歌手,四種和聲。
我想要將所有消失的輪廓分明的聲音,已經釋放到世界上的振動,但從未在留聲機的管子和唱針上,從未被打蠟。我還想要多年前的聲音記錄:大衛第一次在酒吧對我說出他的名字。大衛要我去他的公寓。有一天深夜問我他是否應該參戰,我說是,因為我認為那是他想聽到的。聲音的歷史,每天都在失去。我開始把地球想像成一個蠟筒,太陽是一根針,放在地球上,描繪出一天的音樂——人們爭論、烹飪、大笑、唱歌、呻吟、哭泣、調情的聲音。在那之後,數百萬熟睡的人無聲掃過,像靜電一樣席捲地球。
隨著幾週過去,我注意到了大衛黑暗的一面,我認為他想要竭力隱藏起來。他的手有些顫抖,他很艱難的去捲煙,好幾次了,我醒來的時候,看到他正站在離我們不遠處的地方,他像是月色下的一根石柱,如同古老廢墟中的那樣。當我們在一個城鎮到另一個城鎮的路上唱歌時,他會在某一段中停下,重複最後一行,尋找下一行。有一次我悄悄地走到他身後,他像觸電一樣驚跳起來。我認為那是戰爭,就如同它對許多人的那樣。
有一天,他不再想沉默,我問他是否開槍射向某人,他只是將手舉向空中,而沒有回答。
在八月的末尾,大衛要返回學院教書前的一周,我們只剩下三個蠟筒,我們正在前往靠近花崗岩採石場的沿海小鎮附近的一所房子。我們尋找到了約翰的房子,他是一個名叫瑪麗威廉的女人的堂兄,瑪麗說,他腦袋中有一堆的歌,他的妻子羅斯瑪麗是方圓100英里最好的廚師,她會將一切安排妥當。
鎮上的一些小孩把我們帶到了一條長長的土路盡頭,那是一個非常寒冷的夏季夜晚,來自於幾個月之前的風已經把這塊土地吹得陣陣寒意。我們整天在水面上看到的霧氣已經散去,房子坐落在樹林里或者確切的說是棚屋,一個由隔板拼湊而成的有波紋的金屬屋頂,數十隻鹿角被釘在外面,一隻狗被拴在泥濘院子裡的木樁上,他突然被驚醒,並向我們跑來狂吠不止。最後由於鍊子拴的很緊,他又只能慢搖回去,一群黑鳥從房子周圍被雨淋濕的樹上飛起,然後在更遠處的樹林裡消失,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大衛去敲門,但沒有人回應,於是他在房子周圍轉悠,然後走進的樹林。
「我們走吧」。當他回來時我對他說。現在回想起那棟房子時,我似乎記得,那棟房子沒有任何的窗戶。
狗一直在叫,拉扯著鍊子,他不斷跳躍著,讓自己被扯到難以呼吸,氣喘吁籲,一隻巨犬,我想是一隻熊狗,它是黑色和棕色的,它的胸部是白色的,耳朵看起來像是被剪了。
“閉嘴”,大衛朝著狗大叫,“讓我們等下,直到他們回來”,他一邊說一邊轉過身來凝視著馬路,“我並不認為我們還能繼續走,我感到很
很渴,我們水也沒有了,我們就在這裡等。」
他放下了背包坐在門前的階梯上,拍拍口袋掏出菸絲,然後捲了一支煙,他閉上眼睛靠在門上休息。
我將錄音機小心地放在地上,坐在他的身旁。
然後,自從認識彼此以來,他第一次問我,是否認為我們在這趟旅行後還會再見面。
我說,我希望能再見面。
他問是否會擔心我們正在做什麼。
我說沒有,因為我從來沒想過。
他在門上摩擦著頭部,好像在做按摩。在他前額滲出骯髒的汗珠,他將雙腿併攏放在胸前前傾,將下巴放在膝蓋上,閉著眼,好像在祈禱。
“我羨慕你”,他說。
狗一直在叫,狗鏈叮噹作響,我剛想問他要做什麼,他就大喊道:“閉嘴”,他對著狗,然後爬起來大步走向它。
大衛走進它時,狗抬起頭他的後腿,緊繃的狗鏈迫使他直立,就像一個即將落下的斧頭。
“你在幹什麼?”我說:“小心!”
大衛伸出手,慢慢靠近。這隻狗被它的項圈壓得喘不過氣來。大衛站在那裡看著它,離它只有一英尺遠,然後把香菸彈到狗的腳邊。
然後一個人從森林的邊緣喊道,“嘿!”
我跳了起來。大衛轉過身。狗安靜了下來。
這個男人留著長鬍子,大部分是白色的,但有黑色條紋。他肩上扛著一根長桿,上面掛著死兔子。他一手拿著槍。
「你到底在做什麼?」 他說,放下桿子,用兩隻手舉起槍。
「你好!」 大衛興高采烈地說,就好像沒有槍指著他似的。「我是大衛‧阿什頓,這是里昂內爾‧沃辛。我們是你表妹瑪麗康威的朋友?」
“瑪麗。」 約翰溫斯洛說。「嗯?」他把槍放在身邊,拿起綁著兔子的手杖。
「你一定是約翰,」大衛說。“我們正在收集歌曲,瑪麗說你有幾首?”
「不感興趣,」約翰說。我注意到,他以一些伐木工人的那種緩慢而有目的方式向我們走來。就像他比我們其他人更能感受到一天的長度,並且不需要著急。
「這只需要一點時間,」大衛說。“我可以問一下你在哪裡學的歌嗎?”
「不感興趣,」他又說了一遍,將桿子靠在房子的一側。兔子——一共有三隻——一定是剛被殺死的。血從一隻兔子的嘴裡滴下來,拍打著枯死的樹葉。
“瑪麗說你的家人來自愛爾蘭西部?” 大衛說。
約翰沒有回答。從腰帶上抽出一把刀,從桿子上砍下兔子,把它們並排放在門廊上。
「哪個城鎮?」 大衛問。「我在那裡待了一段時間,回來的路上。那是我第一次學習「牧羊人之歌」的地方。或許你知道?」
「現在看,」約翰說,第一次盯著大衛看。我當時看到他的一隻眼睛充滿了血,我想是從眼血管流出來的。他的臉頰凹陷了下去。他整張臉抽搐,緊繃,又鬆開。「我對此不感興趣。我告訴過你一次。我又告訴你了。我不是想無禮,在這裡。我看你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如果你是從瑪麗那裡來的。晚點回來,也許晚點回來。一兩週,到時候我可以幫你。」
我認為,大衛的說服天賦只是在於,如果他想要某樣東西,他就無法停止追求。如果不是瑪麗慷慨激昂地建議為約翰錄音,而且我們一個星期內都不會在他家附近,我想大衛就會到此為止了。約翰似乎不像其他人,他們一開始總是因為害羞或多疑而拒絕。相反,他以一種最終的、無情的方式拒絕了。他背對著我們,用刀切開一隻兔子,然後開始扯掉毛皮。
「你老婆在嗎?」 大衛說。“也許她喜歡唱歌?迷迭香?”
那人轉向大衛,手裡拿著刀,渾身是血。在他身後,兔子的皮從後腳垂下來。
「或者水,」我說。“我們的水用完了。能不能給點水?」
他嘆了口氣,一腳踹在地上。
「我是基督徒,」他說。他把刀放在門廊上,然後拖著腳步走上樓梯。打開門,陽光灑進屋內,照亮了一個女人的身體,平躺在房間中央的桌子上。當他走到後面,走向廚房時,他沒有關上門。女人的裙子像桌布一樣從桌子上掉了下來。下擺在從門進來的風中翻滾。她的胸前別著一束花。大衛和我沒有說話,因為我們都一直看著。當我聽到約翰關掉水龍頭的聲音時,我轉身凝視著樹林。
他端著兩個木杯出來了。
「口渴的音樂家,」他說。
「謝謝你,」我說。我避免在杯子邊緣留下血跡。
他拿起刀繼續給兔子剝皮,最後把皮從腳上扯下來。當他把它扔到樓梯上時,它落地時濕漉漉的。
“這就是你所做的,去請人們在管子裡唱歌嗎?”
「嗯,」大衛結結巴巴地說。「是的,我喜歡。但他他不是。」 他指著我。「這個是歌手。他可能擁有新英格蘭最好的聲音。」
「是這樣嗎?」 約翰說。將刀刺入門廊,使其直立。他的雙手,撕下了第二隻兔子的皮。「來吧。那就給我們唱首歌吧。」
水嘗起來有金屬味,很苦。
「我不知道該唱什麼,」我說。我的腦袋裡還滿是桌子上那個女人的形象。
約翰開始研究另一隻兔子。「我相信你會想到一個,」他說。
腦海中浮現的第一首歌是“蘭德爾勳爵”,這是大衛最喜歡的歌曲之一。在我們躺在他公寓床上的難得一見的早晨,在我醒來之前他沒有離開的那個早晨,他教會我的。
「哦,蘭德爾勳爵,我的孩子,你去哪裡了?」我唱歌。我閉上眼睛,嚐了嚐燒焦的奶油,看到了淡綠色。“你去哪兒了,我英俊的年輕人?”
「天哪,」我聽到約翰在一百英里外的某個地方說。然後我意識到我沒有唱完整個旅程。
「我去了格林伍德。媽媽,快給我鋪床。
因為我打獵累了,想躺下。
「我的孩子,蘭德爾勳爵,你在那裡遇到了什麼?
是什麼遇見了你,我英俊的年輕人?」
「哦,我遇到了我的真愛。媽媽,快給我鋪床,
因為我打獵累了,想躺下。
民謠冗長而重複,母親用問題訓練兒子,試圖弄清楚為什麼他感到如此噁心和疲倦。他告訴她,他的愛人為他做了炸鰻魚當晚餐,當狗吃了他的殘羹剩飯時,它們都死了。母親告訴他,他中毒了。他同意了,並再次要求她為他鋪床,這樣他也可以躺下來死去。他告訴她,他要把家裡的乳牛留給她,把金銀留給妹妹,把房子和財產留給弟弟。母親接著問道:「我的兒子,蘭德爾勳爵,你給你的真愛留下了什麼?你給你的真愛留下了什麼,我英俊的年輕人?」他回答說,
「我把她的繩子留在你那邊的蘋果樹上,好讓她
掛在上面。媽媽,快給我鋪床,
因為是她毒害了我,我寧願躺下。」
當我完成並睜開眼睛時,約翰和大衛都在看著地面。天空呈現紫色。
「我對你失去親人感到抱歉,」大衛當時對約翰說。
「謝謝你這麼說,」約翰說。
大衛看著我。「挺會選歌的,」他說。「戀愛中的毒藥。」 他的手臂穿過背包的帶子。「我不認為你會一直記得那個。」 他舉起背包,把它放在肩上。「奇怪的是,他直到最後都稱她為真愛。殺害他的兇手。」 然後他轉身離開,沿著路走,經過沉默的狗,沒有等我。沒有說再見或感謝,就像他通常對我們的招待我們的人所做的那樣。
即使約翰對大衛的突然離開感到不安,但他沒有表現出來。
「一首美妙的歌,小伙子,」他說。「這歌我也知道。不過,你改編了結局。」
「是嗎?」 我只是唱了大衛教我的。
「結局通常是,『我離開了她,留下了火與地獄。” 不是蘋果樹和繩子。我想我更喜歡你的版本。稍微溫和一點。」
「謝謝你,」我說,走到留聲機前,把它放在我的背上。
他整個人都在動,就好像他要說的話都梗住了,卡在了喉嚨裡。「祝你好運,小伙子。」
又是一陣冷風吹過樹林,彷彿八月已經過去了。
在波特蘭火車站,我告訴大衛我可以在緬因州多待一會兒,幫他對錄音進行編目。如果他需要幫助,我可以在校園附近找到一間公寓,待到秋季學期。但我應該更直接。這一次,我應該是指給他指路的人。如果不住在緬因州,我本來可以告訴他和我一起去波士頓。也許事情會變得更好。相反,他出於我後來才明白的原因搖了搖頭,並說明年夏天我們會再次收集歌曲。他告訴我,我們會在一次錄音。
9 月到 12 月是肯塔基州果園一年中最繁忙的時期。那段時間大衛沒有回我一封信,所以在一月我寫信給鮑登音樂系。我解釋說我是大衛的研究助理,也是音樂學院的畢業生,去年夏天我是和他一起參加歌曲收集之旅的人。我問,能不能把他的地址傳給我,因為我可能弄錯了,還有一些文件我想分享一下?諸如此類的謊言。
幾週後,我收到了很友善的回信。系主任寫道,他很遺憾成為傳達大衛於 1919 年秋天去世的消息的人。他接著說,他很遺憾地說他不知道我指的是什麼留聲機——大衛的工作一直是教授音樂作曲,而不是民族音樂學,而且院裡沒有贊助一次歌曲收集之旅。很抱歉,我不能提供更多幫助,他寫道。如果我找到你提到的留聲機,我一定會用你留下的方式轉交給你。
我把信折好,走到外面,朝果園走去,然後意識到我不想去果園,於是走到藍色涼亭,但那也
不是我想去的地方。我最後來到了離城數英里的外祖父家。我們喝了茶。他向我展示了他的狗學會的新把戲——用一根棍子抵住他的鼻子。我沒有告訴他這封信的事。他說我“有點恍惚”,問我是不是喝醉了,當我說沒有時,他給我倒了一杯威士忌,然後說:“那你喝醉吧。「 那天晚上我睡在他家,隨後又睡了幾個晚上。
在與院主任的後續通信中,我發現大衛有一個未婚妻,而且他在我們旅行前的春天就訂婚了。
在寫完以上部分之後,已經過了幾天。昨天我打電話給哈佛皮博迪博物館的一位朋友,我知道他可以使用留聲機。他讓我過去,因為這東西太重,無法拖到我家,而且他不確定他能否獲得將它從博物館中取出的許可。
我帶著裝著蠟筒的盒子走了五個街區來到博物館,在門口遇見了他。他帶我經過新的鳥類收藏品,經過骷髏和玻璃花,進入後台辦公室。
「我從小就沒有用過其中之一,」他一邊說,一邊從留聲機上滑下防塵布。
他幫我把第一個蠟筒安裝到旋轉器上。他將管子鉤在唱針底座上,然後將唱針放在圓柱體上。把手放在曲柄上,轉動它。從喇叭裡傳來的是來自50年前的一個男人的聲音,他出生於波特蘭北部的一個海濱小鎮,唱著一首,如同第一次聽時,那樣清晰,並且讓人無法忘懷的民謠。
每個圓柱體的末端都被標有歌手的名字和錄製日期,這就是為什麼我的目光長久停留在最後一個盒子: 1919年10月20日——那是我在火車站和大衛告別的一個月之後的日期。
「讓我們聽聽這個」。我說,我指了指這個蠟筒。
“你好,里昂。」大衛低沉的聲音從房間傳來。
我的心疼痛不已,像是被踢了一腳。那些無法忘懷之事,如同幾年前,我出車禍時,讓我大腿熱血沸騰一般,那種刺針般的疼痛,讓我的大腿不住的顫抖起來。
這個留聲機的金屬喇叭,刺穿了沉寂,我整個人深深陷入了靠椅之中。
「還好嗎?」我的朋友問。
我微笑地點了點頭。
「這個夏天,謝謝你」。大衛說。這來自於
50年前的聲音。「對於去年,我很抱歉。我知道,那時,我和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有些不一樣了。有些事情發生了,但是我無法改變。有些地方,不可避免的腐爛了。
超時的沉默,似乎禁止一般,他好像在思考,沉默就好像是G調。
“我無法去看周圍”,大衛說,“地平線保持著一種特有的速度超速前進”。
更沉默,然後他開始哼唱。
「他在唱什麼?」我的朋友問。
“《死寂冬夜》”。我說。
我閉上眼睛,往靠椅更深處靠去。
一個朝東離去,一個朝西延伸」。大衛用他那低沉的男中音歌唱:「在樹根深處,有兩個靜止的身影。」
我嚐到了鹽和煙草的味道,看到一個靛藍的圓圈變成一個深橙色的棍子,然後突然變成一個黑點,我的嘴裡充滿了潮濕的寶石味道。
我並不知道,自己期待聽到什麼,想要聽到什麼,但是腦海中浮現了一個關於留聲機的著名故事,留聲機是愛迪生惟一一個,剛發明就被應用的機器,他提出了唱針在表面抖動的概念,並讓工程師模擬了這個,第一次就實現了。正是它——它樸素的物質性,那些被大衛聲音造成的細如髮絲的狹口——我專注於他,看著旋轉器上如同膚色的圓筒,愛迪生並沒有想他會被用於音樂,他想像大衛所做的事:記錄信息可以將它放在將死之人的面前來聆聽他的遺言,或者可以記錄一個嬰兒的牙牙聲,然後記錄他在二十年之後的聲音,然後是老年時代的聲音。這樣你就能夠在一個神器中擁有整個生命。
他將成為那些在世的人的一種安慰,但這並不是一種安慰,他不過是一種提醒,提醒我那些我以為已經放下的事,我應該留在波特蘭的火車站,或者強迫他和我一起回波士頓。他不過提醒我,我還是真實地愛著大衛,我對喬治和克勞利斯的感情是深思熟慮的,他相對於大衛刻入骨髓的聲音相比,是如此的不值一提。我將如何放下?一種明確的悲痛,並不是傷感,也不是悲傷,而是一個突然而又明顯的事實,那就是我的生命比原來的短了一寸。當我20歲,那是我最美好的年齡,帶著蠟筒走向博物館,我想我可能會透過翻閱那個夏天的聲音回憶錄來安慰自己,舒緩悲痛,聽到瑪麗康威或泰特爾夫婦的聲音會縫合傷口,就像我和克勞麗斯分手後,在哈佛廣場相遇一樣,我為這段可能變為長久友誼感到高興,如同喬治一樣,他定期給我發他在薩凡納的生活,對與我在一起的日子,他只想說聲謝謝。但這個留聲機提醒我──我錯過了我所不知道,但那卻是大衛的一部分,那真正的生活。他是那麼可笑的短,只有兩個月,那些關於螢火蟲以及在瀑布下裸泳的記憶,似乎什麼也沒有留下,但卻在我多年以來建立的滿足感薄膜上留下了一個美好而又長久的缺口-一個美滿的家庭,一個成功的事業,好的鄰居,好的友誼,一個虛度的人生,這也許就是為什麼人們開始使用留聲機記錄音樂:為什麼要去聽你所愛但已死去的人的聲音。
音樂停了,唱針也停了。
「你還想聽其他的嗎?」我的朋友問,它拆下圓筒並用紙包好。
「還有哪個比較特別的嗎?」他旋轉著這些圓筒,查閱上面的標籤。
儘管我喘不過氣來,但我還想要聽到更多,就像狗啃骨頭,直到啃到骨髓為止。
「那就讓我們從第一個開始聽吧。」我說。
我看著窗外的街道,在人行道上仍然有絨毛般的白色泡泡,在尋找一個落腳之處。
以上所述便是我們對於電影《時光留聲》原著小說介紹的全面介紹,如果您想要深入了解這部作品,包括劇情發展、人物性格分析以及劇情解讀等方面的內容,我們非常歡迎您持續參觀我們的台詞課,我們將會提供更詳細、更全面的分析和評論。
網站聲明: 本站“電影《時光留聲》原著小說介紹”由"天使的誘惑"網友提供,僅作為展示之用,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果侵犯了您的權益,請來信告知,我們會盡快刪除。
- 1 動漫《我獨自升級》每週幾更新
- 2 Netflix《愛愛內含光》角色介紹
- 3 《難哄》追劇日曆
- 4 泰劇《禁忌摯友》第1-12分集劇情(含結局)
- 5 《逆光涅槃》劇情介紹
- 6 《六姊妹》追劇日曆
- 7 《難哄》全集劇情分集介紹
- 8 韓劇《Sweet Home 3》確定7月19日上線
- 9 《仙台有樹》追劇日曆
- 10 《偷偷藏不住》桑延的車
- 11 《樹下有片紅房子》追劇日曆
- 12 韓劇《抓住你的衣領》第1-16全集劇情(含結局)
- 13 《愛愛內含光》全集劇情分集介紹
- 14 《從贅婿到寵臣》劇情介紹
- 15 《年終獎五百萬》劇情介紹
- 16 《行至愛意消散處》劇情介紹
- 17 《薔薇風暴》第6集分集劇情介紹
- 18 《白色橄欖樹》男女主結局
- 19 二虎和溫如玉的短劇叫什麼
- 20 《於氏王後》驚艷畫面是哪一集?
